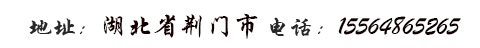最美老家99那年东湾子的烧年糕
|
也说年糕 文/庄元 日前,在《老家热河》上看到一篇关于年糕的文章,感同身受,同时也勾起了我童年时一段美好的记忆。 五十年前,父亲在双塔山麻袋厂上班。厂子为了解决原材料不足的问题,在丰宁县洪汤寺成立了一个亚麻厂。父亲被调到亚麻厂工作,母亲领着我们弟兄四个也来到了亚麻厂,住在一个叫东湾子的小山村。租住在村东头一个老乡家,这是典型的三间房子两铺炕,进屋先进厨,有一道风门子,两扇对开的门,然后是一边一个锅台,外头屋后墙跟并排放着三口大缸,一口装水,另外两口装粮食。缸空(kong四声)放着一些农具。 我们住西屋,房东住东屋。东屋靠北墙放着一口三格躺柜,柜上有两个掸瓶,还有几个空酒瓶子,那时很少有人喝瓶装酒,酒瓶子都成了装饰品。躺柜前有一个春凳,靠东墙放着一个箱子,上边放着一个老式梳妆台,箱子和炕沿之间有一个酸菜缸,一个炕桌四脚朝上放在酸菜缸上,当酸菜缸盖,炕稍是被物垛,上面苫着一条打着补丁的毯子,炕上的炕席坏了一个洞,炕头铺着一块牛毛毡,挨着炕沿这头纤着一块布,布的本色已经看不出来了。一个泥火盆放在炕沿边。火盆边上有两副火筷子,一副是铁匠炉打的,手拿的部分是四楞的,一条细铁链把两根筷子连在一起,另一副是八号铅丝做的,每根一头上弄了个圆圈。窗台上有一盆葱,还有一个大盘子里边摆满了扒了皮的蒜瓣,下边泡着水,上边长了有一拃长的蒜苗。窗子由四部分组成,中间大,两边小,大窗又分上下两部分,下边是固定的,中间有块玻璃,上边可以向上翻起,两边两扇小窗可以平开,冬天小窗不开,为了保暖小窗和窗框之间的缝隙是用纸糊上的。 入住的第一天,当时好像是还没出正月,父亲母亲收拾房子归置东西,房东大娘让我们到东屋炕头上坐,用火筷子把火盆里的火扒拉扒拉,让我们烤火。 大娘说:饿了吧,等我给你们烧年糕吃。 我觉得很奇怪,年糕还能烧着吃吗? 一会大娘从外边拿进四个黄黄的东西,大小和鹅蛋差不多,椭圆形,扁的。每个形状还有微小的差别,有的一头稍尖,有的两头都尖,有的两头都不尖。 我问:大娘,这是什么呀? 大娘:年糕呀。 年糕怎么这样呀,在我的印象里年糕应该是一片一片的呀。 大娘从酸菜缸里捞出一颗酸菜揪下四个酸菜叶,把四个年糕包上放进火盆埋在火炭里。屋里弥漫着酸菜的味道。 大娘对我说:你开开窗户,摘一串小干鱼。 我按着大娘的指导拉开大窗户的上半部分,站在窗台上探出身子看见房檐底下挂着很多弯成弓形的木棍,弓弦上穿着小干鱼,我摘下一弓鱼递给大娘。 大娘说:再摘一串带腿的。 我看见真有带腿的,摘下来递给大娘。 我问:大娘这是什么鱼呀? 大娘说:泥了沟子(泥鳅) “这个带腿的呢?“ “小蛤蟆“ “能吃吗?“ “能,香着呢“ 大娘解开绳头把小鱼和蛤蟆撸下来,放在火盆沿上,把铅丝做的火筷子并排横搭在火盆上,把小鱼和蛤蟆棑放在火筷子上烤。 三个弟弟靠着炕头墙坐成一排,看着眼前的一切,听说有吃的,更是充满了期待。 大娘不时翻动着小鱼和小蛤蟆,一会飘出了香味。 我问:啥样算熟了呀? 大娘:你看像这样发黄的就熟了。 我也帮大娘翻动小鱼,把熟了的放在火盆沿上,待都烤好了,大娘用火筷子扒出埋在火里的年糕,这时包着年糕的酸菜叶已经糊了,大娘用扫炕笤箸逐个扫掉已经烧糊了的酸菜叶,吹了吹灰,也放在火盆沿上。 大娘:凉凉再吃啊,热! 过了一会,大娘拿起一个年糕试试温度。 “好了,吃吧,烧年糕,就小鱼。”说着递给我们每人一个。 我们谁都没有接,三个弟弟看着我,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不经过大人准许,是不可以吃别人给的东西的,我也做不了主。 “妈!妈!” 妈妈应声进了东屋,“干啥呀,又捣蛋是不是?” 我说:大娘给我们烧年糕吃。 大娘:这孩子,真懂事,吃点东西还得问大人,我给他们烧个年糕,烤几条小鱼,先垫吧垫吧。 我妈:噢,吃吧,谢谢大娘。 我们齐声:谢谢大娘。 大娘:谢什么谢,快吃吧。 年糕外边一层是硬的嘎吱里边又软又粘,还包着馅,一头尖的是酸菜馅、两头尖的是豆馅、两头都不尖的是萝卜馅。烤小鱼特别香,小蛤蟆比小鱼还香,肚子里还有籽。 “妈、爸你们快尝尝大娘家的年糕和烤小鱼特别好吃!” 妈在西屋应道:你们吃吧,别胡作(zuo一声)乱闹啊! “哎!”我们齐声答应。 我边吃边问:大娘,这年糕是怎么做的呀? 大娘:大娘我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你等着,等到了冬天,进了腊月门,家家户户都淘米压面撒年糕,到时候你一看就知道了。 从正月一转眼就到了腊月。 我也见识到了年糕的制作过程,前面的过程都一样,但是,蒸的时候有很大的区别。我们老家(隆化张三营)锅里填满水放上篦子,在篦子上均匀的撒满煮好的红芸豆,空隙的地方撒红小豆,尽量减少空隙以免撒面的时候落到篦子下面的水里,在豆子上撒黏米面,撒到一半的时候零星的放几个大枣,面都撒完了,最上面再撒一层红芸豆。大娘他们不撒豆子,把黏米面攥成小面团,一个紧挨一个的摆满篦子,盖上锅盖,蒸几分钟,打开锅盖,看到面团变颜色了,用筷子把面团夹开,铺满篦子然后再在上面撒面。中间不放枣,上边也不撒豆。熟了之后,用铲子沿着锅边转圈铲一下,然后需要两个老爷们一边一个提着篦子绳把年糕提出锅,有人将一块刷过水(防止年糕粘上)的大木板盖在年糕上然后大家合力将篦子翻过来,取下篦子,抬着板子和年糕放到屋里炕桌上,用菜刀粘上水切掉年糕周围的嘎吱。这时,包年糕“大战”开始了。谁家撒年糕全村的姑娘媳妇都会过来帮忙,炕上放着几盆馅,有酸菜(剁碎用猪油加葱姜蒜拌过)豆泥(红芸豆红小豆煮烂捣成捣成泥状,加糖精)萝卜(擦成丝,开水焯透去味加佐料拌好)等,还有一盆凉水!我在旁边仔细的看着。 过程是这样的:左手在馅上(菜馅上蹭蹭,不能在豆泥上蹭)右手在凉水盆里沾一下马上到刚蒸出的年糕上揪下一块,放到左手上,右手也到馅上蹭蹭,然后迅速地双手把年糕拍成圆饼状放上馅,捏拢,团成椭圆形再按扁,根据馅料的不同做成一头尖两头尖或者两头都不尖的,馅和形状要统一。包好的放到盖顶上,端到外边晾凉了,装在缸里储藏起来。 我问大娘:干啥又蹭馅又沾凉水的? 大娘:蹭馅是为了不粘手,因为馅上有油,沾凉水是不烫手。 我说:晾凉了不就不烫手了吗? 大娘:傻孩子,凉了就包不上了,不和炉了。 我明白了,来这么多人帮忙就是为了趁热呀。 包好的年糕、蒸好的豆包、两步粘、小锅饽饽、冻豆腐、猪肉等都放到房檐下的一口大缸里,缸上盖着一个石板做的缸盖,上面还要压上一块石头。这些就是一家人的年过货。一般的家都能吃到来年出正月。 烧年糕是哄小孩的,正餐都是熥着吃,如果熥好了再用油煎一下那就更好吃了。 这些年,因为工作需要东奔西走去过很多地方,各种风味的年糕也吃过不少,但是,当年房东大娘的烧年糕是我平生最最难忘的。 (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庄元。隆化张三营人,现居北京。 总编辑:王冰玉王琦承德罗锅 副总编:贺成利何英华 闫春生彼岸花 责任编辑:丁海陈怡良 百伶大咩 法律顾问:宋连生 (山庄律师事务所) 合作-投稿邮箱:qq.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amazia.com/ymzsy/12116.html
- 上一篇文章: 帕提亚帝国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