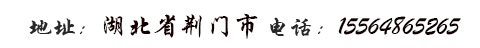杨飞云amp佟芃芃画家夫妇的相处
|
在艺术家的圈子里有一条不成文的定律:艺术家的妻子不好当。太出风头,容易对丈夫产生影响;太过低调,又很难与丈夫找到共同语言。不过对杨飞云和佟芃芃这一对艺术圈的模范夫妻来说,这条定律早在结婚之前就已经不存在了。 “十二岁那年,我被领到他面前学习绘画。那是一个夏天的中午,阳光很明亮。他很温和而客气地接受了我这个学生。他那时说话不多,却很勤奋地画画。”当时的杨飞云在呼和浩特铁路局的文化宫当宣传干事,虽然不是专业画家,但是在那一带已经画得很好了。“他画儿画得很好,所以身边跟了不少喜欢画画的男孩子,他们都很尊重他。我年龄最小又是唯一的女孩,混在里面很显眼。”佟芃芃与杨飞云的第一次相遇就是在这样的师生关系下发生的。“第一次是我们当时的主任和她妈妈带她来学画画,第二次她拿着画来给我看。当时我在她身上发现一种很灵动的东西,很能打动我。我喜欢的女孩就是在画面中能表达出一种很秀丽、凝重的东方女孩的感觉,还有那种聪慧灵动。她来了以后,就坐在床边,我一看就说‘哎呀,太好了,你别动,我给你画一张吧。’她就背着书包,一动不动让我画,结果过后一想,我一直也没让她休息,挺累的。”当时的杨飞云不曾想到,这一画,画出的是一辈子的承诺。 乱画的少年 作为当代写实油画的标志人物之一,人们在谈论起写实油画作品时,通常都会拿杨飞云来做比照。然而不管持哪种观点,人们大都同意他承袭了中国写实油画的衣钵。在说到他如何走上绘画生涯时,杨飞云笑着说道,若细算他的绘画生涯,当从四五岁左右开始的“乱画”时期说起,而他的启蒙老师就是他的父亲。 杨飞云的父亲是内蒙古包头郊区一位乡村教师,音乐、美术“双栖”教学。在他教那些小学生画画时,杨飞云总是跟随其后,在课本上和作业本上乱涂乱画。而他的母亲则是一位乡村剪纸的行家里手,每逢年节,她总是受邀为村子里的人家做窗花剪纸。父母常年从事乡村艺术活动的耳濡目染,让杨飞云在年少时代就播下了艺术的种子。 真正开始绘画学习是在“十年动乱”开始以后,而杨飞云最要感谢的,就是三本重要的画册,正是它们影响了他的一生。“一本是徐悲鸿的素描,吴作人先生写的序,还是用文言文写的,当时看那几句话都很难看得懂。第二本是达·芬奇的评传,是当时苏联人印刷的,一个很厚的大16开本,里面有对整个文艺复兴的评价,尤其是关于达·芬奇的。里面还有很多图,因为当时是看不到这种书的,所以当通过特殊的方式拿到那本书的时候,我就临摹里面的每一幅印得很模糊的插图,就是这样一个学画过程。第三本书,也是很重要的一本书,就是伦勃朗的画集。”杨飞云至今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回忆起画册的样子。“很厚,亚麻布的封面。里面都是把油画印在一张纸上,再粘在书上的。那也是吴作人写的序。里面有的油墨都是臭的,可能还是苏联人帮着印的。伦勃朗的很多经典作品都在里面,我都不知道临摹过多少遍了。” 那个时候的杨飞云刚刚十六七岁,“‘文革’完了以后正在铁路学徒。当时还能看到一些苏联方面的书,就是现实主义的那批。可能是那些书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到了现在你要是问我最喜欢的画家是谁,我还是会说达·芬奇、伦勃朗。可能就是小的时候对这些画家有太深的情结了。”正是将古典大师伦勃朗、达·芬奇的画册作为早期学习绘画的范本,才使得他在初学绘画时就具有了很高的艺术鉴赏标准和扎实的绘画功底。 杨飞云《书房》90xcm 默契的夫妻 年,当佟芃芃第一次出现在他面前时,杨飞云惊喜地发现这个女孩身上的沉静、优美正是他一直所追求的,但最重要的是,他发觉他们之间有说不清的默契。“她当模特时,有时对作品比我还投入,比如哪块颜色用得不好,哪些地方她觉得画得不好,她都做评价,所以实际上她参与了艺术创作。说到配合,这可能也是非常奇怪的一点,比如我画到她的脸,画得非常较劲的时候,她似乎能感觉到,就配合得非常好,一动不动,其他模特做不到这一点。她能感觉到你画到了哪个地方,她能一两个小时地配合着你,画到放松时,她也很放松,聊聊天。对我来说,我这一方面是因为画的是亲近的人,另一点是因为她对艺术,对绘画的热爱。” 年,杨飞云考进了中央美术学院,也离开了芃芃的身边,但他们之间仍旧通过信件保持着联系,同时芃芃的绘画水平也在不断前进。“我那时候差几天15岁,除了写信,他一放假就跑回来,一块儿看书、一块儿画画,假期里就画得很多。”杨飞云也会从北京带回很多艺术类的书籍给她,这也加深了她对北京的向往。“年,我考进了北京中医学院中药系,开始了五年的大学生活。我们见面的机会又多了起来。他常常带我去看画展、看歌剧、看舞剧,那时我正处在一个全面吸收知识的阶段,特别爱读书,尤其是外国文学名著。每到周末,我们探讨的话题也总是围绕着文化、文学、艺术以及这些领域的大师们。那时听古典音乐也成了我们相处时光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就是在这样的不知不觉中,我的人生观、理想和爱好被确定下来,以至于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的兴趣和对生活的态度都那么一致。” 在同学们的印象里,上学时期的芃芃是羞涩而善良的,由于读的是医学院,按照规矩,做药物实验后,每个学生都要杀死用过了的实验动物,经常有几十只的小白鼠等着学生们下手。有一幕至今令大家记忆清晰:很少求人,甚至很少和同学说话的芃芃站在同组的男生面前支支吾吾了半天才开口,声音很小:“你们能帮我处死那些小耗子吗?”这个细节概括了芃芃留在大家心中的形象:善良,文静,甚至胆怯,是心甘情愿躲在人群后面的那种女孩。那时候芃芃的同学只是知道作为医学生的她画画很棒,但直到毕业才知道,她嫁的是杨飞云。这段缘分也让同龄人羡慕不已:芃芃说了,一毕业就结婚,什么仪式都不办,把被子抱到杨飞云宿舍就行了。 在之后的若干年里,杨飞云又画了一系列以芃芃为模特的作品,也让大家开始熟悉和认可这一对画家夫妻。“这些绘画,对于别人是一件件独立的作品;对于我们,却像一串珠链,串起和记载的是一段段难忘的时光。那中间有我们的沟通、探讨,也有争吵和突然的开悟。那时我们的生活很单纯,似乎只有一个主题,除了绘画还是绘画,一切以他绘画为中心。精神是充实宁静而快乐的。”这是这对夫妻对这段时光最真实的感悟。 簪花仕女图xcm 追求心灵与诚实 作为一名画家,杨飞云有着两个最为人熟知的身份:一个是写实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个是中国油画院的院长。这就好像他艺术生涯的两面:古典绘画和艺术教育。在谈到古典绘画中“真、善、美”的意义时,杨飞云说:“‘真、善、美’这乍看陈词滥调的东西,正是油画院秉持的核心价值。”画院强调“真、善、美”的背后,正是因为它近来被强调得少了。把文化当作产业运作的副产品,是一种黑白的颠倒和审美的堕落。“无论是绘画还是做人都不能虚假,不能不善。” “真”不仅代表绘画只能表现真实形象,而且意味一种品格和思想,正所谓“上德归真”,是作为艺术家所需的纯粹和作为普通人所需的诚恳;“善”是你在观赏艺术品时能体会到的令人感动的善意动机;而“美”,一方面是存在于宇宙的内在规律,如黄金分割,天然和人的审美本能契合,但若只有这一层面会陷入程式化、概念化的空洞,“美”的另一方面来自人的内在的参与和心灵的感动。因此,“美”的形式是个性化和不同质的。深刻的是美,强烈的是美,批判的也是美,但它们的精神是暗合的。“鲁迅的骂人,因其背后的责任而美,下里巴人的劳动,因其真实、质朴和耕耘而美。这样生发于‘真’、‘善’之上的‘美’,是具有绝对意义的,能够触动心灵,带来心灵愉悦的。”他说。 中国油画院曾举办了《林旭东、陈丹青、韩辛——四十年的故事》《山艺术文教基金会收藏俄罗斯油画巡回展》《寻源问道——中国油画院特邀艺术家联展》《心灵与诚实——油画作品展》等等一系列重要展览,对于杨飞云来说,其中“心灵与诚实”这场展览的命名代表了他内心的追寻。“我觉得这是一个画画的人在今天要保持的一个态度与追求,一个绘画艺术上最基本的追求。诚实,说的就是你的绘画要真诚,要体现出自己真实的感动和感受,是通过观察得来的,不能超前也不能做作虚假。前段时间有人说现在的文化界有三浮:浮躁、浮浅和浮夸。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人们缺少心灵和诚实,所以才浮。” 作为中国油画院的院长,杨飞云同时也在坚持着另一个理念“寻源问道”,这也是油画院成立的宗旨。杨飞云表示:“寻源问道”并不是要固守传统或否定变革,而是对人们离源头太久太远而失去根基的现状的反省。只有汲取了源头的营养才能有真正的创作。只求新的是新闻和娱乐,虽能掀起热浪,却转瞬即逝。有生命力的艺术,必然是有根基、有传承的。因此,在这个主旨之下,油画院成立的首个活动便是以“寻源问道”为主题的油画展,展出了吴冠中、靳尚谊、詹建俊等大家的作品,杨飞云希望将来也能按照这个主旨继续做下去。 写实绘画是心灵体验 尽管写实油画在近两年的市场中成为了人们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amazia.com/ymzgx/12103.html
- 上一篇文章: 东北大环线7天6晚,一起撒欢,来一场
- 下一篇文章: 6认识油脂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