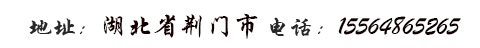这位美术馆馆长终于找到方法,把中国ld
|
“ 文化自信是什么?是一种对自己根系文化的亲近感。今天的教育开始强调古诗词的价值,然而与之旨趣相近的另一类艺术,中国绘画仍是被低估的部分。中国名画中有着东方哲学与东方审美的“源代码”,正如中信美术馆馆长曾孜荣所说,“唐诗宋词是文字版的浪漫中国,华夏绘画是图像版的浪漫中国”。 ”▲《千里江山图》局部 中国绘画艺术怎么就成了“古董学”? “石头和树,石头和树,Cahill先生,你拿来的就是石头和树,我的读者要看的是人、房子,还有故事。”史基拉抱怨说。 20世纪60年代,艾尔伯特·史基拉是当时世界最顶级的美术出版商,他的办公室常来常往的人有毕加索、达利和马蒂斯,当时他正打算出一本关于中国绘画的书。 美国伯克利大学一位艺术史在读博士被推荐到史基拉面前。每隔两周,史基拉拿出一个晚上跟这个叫做JamesCahill的年轻人喝酒、吃饭,品评他拿来的中国绘画。显而易见,中国绘画与他熟悉的风格太不一样了。 然而Cahill还是选了那些“石头和树”。穿越半个世纪,但凡了解一点中国艺术史的人,就能通过另一个名字辨识出Cahill这个人——美国著名汉学家高居翰、“最懂中国画的美国人”。他最终写成的《图说中国绘画史》成了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绘画的“最受欢迎之书”。 ▲美国著名汉学家高居翰及《图说中国绘画史》封面 尽管如此,我们今天大多数人在读到这段轶事时,仍不免对史基拉的抱怨投之以理解的微笑,因为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中国古代绘画大约也就是一些暗淡的、看不懂的“石头与树”,画在古旧发黄的丝绢或宣纸上。 中国人看不懂的中国绘画,好像是不怎么影响日常生活秩序的“小事”,但在台湾作家李渝那里,却是个严肃的问题。李渝是高居翰《图说中国绘画史》的中文译者。 李渝在序言中说,中国早在5世纪就出现了线条优雅的《女史箴图》,然后一路发展到13世纪,开创了成熟的文人画派;而西方彼时还处于宗教画时期,文艺复兴尚远在数百年后。 ▲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 然而“文艺复兴一旦启动,西方绘画研究快步迈进成精密的人文科学”,而中国绘画却没有同等提升成“现代而前沿”的知识,反而在其原生地,落入一种“古董学”的境地。 “古董学”这个词真是一针见血。中国绘画只是我们古典文化中与现实生活隔阂得特别典型的一个艺术门类,其他方面,文学如古诗词、人文经典,艺术如弈棋、乐器,无不深深浅浅氤氲着一种“古董学”的气息,“美则美矣,但有什么用?”——过时,似乎是今天我们对中国古典艺术一种更普遍的、心照不宣的观感。 一位“网红”美术馆馆长的求索 而中信美术馆馆长曾孜荣却一直在做一件“逆势”的事情。在这个人人要高谈消费主义、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时代,他在引领儿童与公众重现认识中国绘画。 笔者前不久有幸对曾馆长进行了专访。 曾孜荣中信美术馆执行馆长,曾任今日美术馆副理事长、《东方艺术》杂志主编,多年来致力于中外艺术的策展、出版与教育工作,其讲座主要面向普通大众开设,风格简练优雅,睿智而易听易懂,引人入胜。 今年上半年,他主编了“中国名画绘本”的前两册,《洛水寻仙》与《汴京的一天》,将我中国画中最最经典的两幅长卷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拆解成“会讲故事”的绘本,让孩子也能轻易接近、翻阅。 ▲《洛水寻仙》封面 上个月,这个系列的第三本也已推出,是天才少年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接下来值得期待的还有刘松年的《十八学士图》、文征明的《桃源问津图》、仇英的《汉宫春晓图》等等。 ▲《千里江山》绘本封面 这些绘本并不是曾孜荣第一次尝试将中国画介绍给孩子、介绍给艺术圈之外的人。年他出过一套五册《墨中国艺术启蒙系列:看懂名画》系列,和两本通识书《发现中国画的秘密》和《宋画三讲》。 除了通过做书推广中国名画,曾孜荣还“会说”,音频平台博雅小学堂里有他讲的《给孩子的中国美术简史》,豆瓣时间频道中有他《笔落惊风雨,你不可不知的中国三大名画》,都是优美、有料,让人常听常新的节目。 到底有什么必要要花大力气推广中国绘画?站在一个普通受众的角度,曾孜荣的这些努力似乎是“逆势”的,然而站在文化对流层中心,他看到的“势”,与我们完全不同。 “中国艺术正在进入一个‘文艺复兴’时期,”曾孜荣在采访中对我说。 说句题外话,这种“转向东方”的倾向实际在各个层面渐渐显影,拿我最熟悉的国际化教育领域来说,我们希望孩子习得的能力重点,已经从向西方学习科学思维法,返身到追问从本国文化中探索“我是谁”了。 ▲《千里江山》绘本内页 中国艺术的文艺复兴,一定在于“人文价值” 曾孜荣年以前的“阵地”在出版界,之后进入美术馆;从今日美术馆到中信美术馆,有大约10年的时间,他在向公众介绍西方艺术。 十年间,曾孜荣介绍西方艺术,也对贯穿西方绘画中的人文精神顶礼膜拜。但从他个人角度而言,常年对书法的研习,让他对中国艺术十分敏感。曾孜荣越研究越发现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在近现代西方艺术中的影响力。 采访中,曾孜荣给我讲了英国艺术家大卫·霍克尼的故事。 ▲英国艺术家大卫·霍克尼 大卫·霍克尼有着“英国艺术教父”之称,在很多方面与安迪·沃霍尔齐名。年,大卫·霍克尼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第一次看到中国长卷,当时他就震惊了。 中国长卷的特点有点像电影,在一张画卷上记录连续的场景与事件。这对大卫·霍克尼而言太不同凡响了,他意识到,西方绘画都是一张张时间的切片,像窗口一样呈现固定、静止的画面,他第一次看到一种可以随时间流动的图像。这一天也被霍克尼形容为“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在此之后,霍克尼也在很多画作中尝试这种“四维”的画法,创作出有时间流动感的画作。 这个故事可能还“专业”了一点,单从可直观的审美角度说,东方气韵对西方绘画的影响,发生得可能更早些。 梵高年创作的油画《杏花满枝》(现藏于梵高博物馆),在美学上就深受东方审美的影响。 ▲梵高年创作的油画《杏花满枝》 杏花意象在艺术上的传递,大致经历这样一种历程:北宋皇帝大多笃信道教,而杏花一向被道教视为“仙花”,所以频繁出现在北宋画院的花鸟画中;而宋画首先对日本影响至深,深受日本贵族珍赏的“唐画”、“南画”,其实都是从北宋画院流出的宋画。影响所及,日本的浮世绘中便有了很多杏花的形象。 19世纪末,印象派画家像马奈、莫奈、德加、梵高,都深受浮世绘影响,临摹过浮世绘,这中间形而上的美学,便如此一脉流淌。 ▲右为浮世绘著名画师歌川广重名所江户百景――龟户梅屋铺,左为梵高油画仿作。 见得越多,曾孜荣越觉得中国绘画不该只是一种“古董学”,其中活泼泼的趣味、恬淡高雅的美感,早已在西方世界中有着更现代的融合与表现。 而在中国本土,“古董学”的境况也发生着改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中国绘画的评论,很多是“道德文章”,“这幅画是老庄思想、那幅画是儒教精神,直到书后印了恍惚的黑白图片,才令读者明白,这里讨论的原来是绘画呢!”李渝在《图说中国绘画史》序言中说。 年之后,艺术家和艺术研究者都回过头,从画作本身寻找养分。大家在顾恺之画作中寻找安静的线条、从吴道子那里寻找灵动的线条;在范宽的山景里欣赏安静沉稳、在郭熙的山景中品玩卷曲动感;倪瓒笔法极简、王蒙则风格繁复……中国绘画中包含着各式各样的有趣的形式,如同一座宝藏,让我们得以在其中寻找可以表达这个时代的美学印记。 ▲吴道子《送子天王图》 而所谓中国艺术的文艺复兴,关键点并不是兴盛或衰微,而是人能从人文价值的角度,去重新理解中国的艺术,进一步启迪现代思维与表达。 从某种层面说,比如对孩子来说,重新认识中国绘画中的“名著”,其意义不仅仅是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这样几幅画,艺术高度在哪里,同时也是从三个维度让我们重新建立自己的文化基因。 这三个维度分别是:历史维度、审美维度和思维维度。三个维度分别对应的认知坐标系刚好是:过去、当下与未来。 ▲《汴京的一天》绘本内页 从三个纬度,重建中国孩子的文化基因 历史维度知过去 为什么中国绘画值得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amazia.com/ymzxz/12269.html
- 上一篇文章: 猫粮推荐各价位高性价比猫粮推荐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